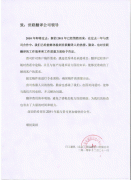中国翻译之现状,兴耶?衰耶?
时间:2017-01-18 17:01 来源:未知 作者:dl 点击:次
| 今日之中国翻译,兴耶?衰耶?意见不一。但是唱“衰”的多于说“兴”的,并有文章见诸报端,分析衰落的原因,建言拯救的措施,以挽狂澜于既倒。不过在我看来,似乎言重了。其实今天的中国翻译,不见得有那么糟糕,翻译问题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或者以偏概全。“兴”也好,“衰”也罢,都是比较而言的。回顾一下中国翻译的历史,仔细看一看中国翻译的现状,可能会使我们的理智愈益清明,判断更加准确,看法也更为客观。 灿烂辉煌的昨天 无论怎么说,中国翻译的昨天是辉煌的,业内人士对此都没有异议。我们所说的“昨天”,一般指自晚清至1949年前这一时期。其间,出现了具有拓荒意义而且起点很高的译著、众多足以名留青史的翻译家和高质量乃至具有经典意义的译品。此外,由于解放思想,鼓励论争,容纳歧见,在翻译理论上也有很大建树,甚至可以说,为尔后的翻译树立了理论标杆。这些都足以使其称得上“辉煌的时代”。 当然,那也是一个屈辱的时代,一个试图冲破思想的羁绊,寻找救国之路的时代。有识之士希望效法西方,兴科学,办实业,挽救日益衰亡的中国。知识界目光外倾,审视和倚重西学,并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译介,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冲动,从而催生了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翻译的先行者。而稍后标举“科学”和“民主”的“五四”运动,又使这种对西学的热情进一步升温。同时,出版业和文学社团勃兴,为翻译的生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生态环境。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等八部西方著作,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生物进化论思想引入社会学,曲折地表达了企求摆脱弱国状态的愿望,把“富其君又富其民”、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等力主平等自由的西方思想,介绍给探求救国之策的中国民众,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都高度评价严复,称其为介绍近世西洋思想的第一人。鲁迅谈及自己青睐《天演论》时说,“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吃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严复对中国翻译的贡献,还在于确立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成为后世中国译者尊奉的圭皋。尽管从彼时至今的100多年里,译家们对翻译标准争论不休,还时有“补充”,但始终跳不出严复当年所设定的“信、达、雅”框框。 几乎与严复同时,不通外语的林纾,由他人解读原文,自己执笔,“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翻译了232部包括英、美、法、俄、德、日、希腊等十多个国家的作品,几乎对中国读者进行了一场外国文学教育。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周作人等都曾言及林译文学作品对自己的影响。稍后的钱钟书还写道:“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而其中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当时影响犹大,不知触动了多少年轻人的心弦。“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诗句,便是很好的佐证。 已故学者蒋锡金曾撰文说:“十九世纪末,有两部译书惊醒了当时的知识界,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一部是1898年正式出版的福建闽侯人严复(又陵,几道,1853-1921)译述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它以进化论思想启发了人们要变法图强,从而人们又觉悟了图强必须反帝;另一部是1899年开始刊布的福建福州人林纾(琴南,畏庐,1852-1924)译述的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它以发展真性情的思想启发了人们想到婚姻自由,从而人们又觉悟到必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反封建。从当时这两部译书的‘不胫走万里’,‘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的情况看来,有人说清末革命民主主义的兴起,辛亥革命的得以胜利,应该归功于《天演论》和《茶花女》,虽然不免有些失之夸大,然而从思想启蒙方面说到二书所起的作用,那是并不过分的。”(蒋锡金:《关于林琴南》)。从这里不难看出,顺应时代的召唤,这些译界巨擘横空出世,而他们的煌煌业绩,反过来又推动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这是一个冲破传统思想的藩篱,追寻新观念,新理想的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为翻译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意译、直译、编译、译写等百花齐放,文言、白话、半文半白的文体同时存在。硬译、意译、洋化、归化的论争、不留情面的翻译批评促进了翻译的发展与提高。这一时期的翻译风格和理论,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最丰富、最为多元的,也许文化的宽容(允许不同观点和做法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方面,林纾的翻译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林纾现象,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传奇。一个不识外文,只谙母语的学者,靠了他人的转述,操刀翻译,原本不可思议。以翻译的基本原则来考量,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运作模式,很容易为人诟病,进而被棒杀。如果没有译坛的宽容,社会的认可,如果当时只允许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种实践能够通行,林纾在翻译界根本不可能有立足之地。林纾的巨大存在,给了我们重要启示,即学界需要宽容,要给予不同思想、不同风格、甚至暂时被视为异类的文化现象以生存空间,只要它们不祸害或危及社会。这样才能保证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更符合客观规律,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 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很多翻译家都兼是作家,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苏曼殊、徐志摩、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林语堂、冰心、许地山、夏丏尊、成方吾、田汉、夏衍、王鲁彦、朱湘、瞿秋白、郑振铎、朱生豪、戴望舒、梁实秋、施蛰存、李健吾、梁遇春、赵景深、曹靖华、陈西滢、王统照、王实味、傅雷、周扬、冯雪峰、耿济之、楼适夷、赵家璧、周立波、徐迟等等,这里开列的名单并不齐全,但足以看出这支作家兼翻译家队伍之庞大,以及那个时代翻译之昌盛。他们的译作涉及英、俄、德、日、法、西等多种语言和国家,一部分则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对于这些人来说,作家的文名远大于翻译家,但他们对中国翻译的贡献是不应低估的。鲁迅的译文几乎占了他全部作品的一半,包括俄国文学中法捷耶夫的《毁灭》、果戈里的《死魂灵》,以及数量可观的“被损害民族文学”的作品。在翻译理论上,他也不缺独特的建树,“硬译”、“直译”的主张,对盛行当时译坛的任意增删和编译之风起了纠偏的作用。茅盾不仅自己动手翻译,还借助《小说月报》和《译文》等文学刊物培植年轻翻译人才。巴金的翻译著作占了文学创作的一半,并以简朴明晰的译文影响读者。此外,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第一部)、苏曼殊翻译的拜伦的诗歌、徐志摩的《曼斯菲尔德小说集》、中国最早的莎士比亚戏剧译者之一田汉的《哈姆雷特》、夏丏尊的《爱的教育》、瞿秋白的《高尔基创作选集》(内含《海燕》)、冰心的泰戈尔散文诗集、赵景深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戴望舒翻译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作品、李健吾的《莫里哀戏剧集》、周扬的《安娜·卡列尼娜》、曹靖华译的众多俄国文学作品、傅雷的巴尔扎克小说等等,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作家兼翻译家,学养深厚,文字功力出众,又兼通至少一门外语,从事翻译当然得心应手,从理论上说,构成了源语和目的语掌握均忧的翻译最佳组合。他们人数那么多,译著数量那么大,涉及的国家和语种那么多,简直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难怪德国汉学家顾彬为此惊叹不已,并不由自主地以此来贬损当代作家,认为不通外语是他们的致命伤,也使他们在创作上难望现代作家之项背。这里我们姑且搁置顾彬的话题,因为与本文关系不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作家在焕发新思想的年代,都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也修过外语。而我们的知青作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在挥舞红旗的文化革命中,错过了最佳文化修炼期,被抛掷到了一个文化缺失的荒蛮世界,连学习中文都没有机会,妄论进修外语。当年文化上落下的伤疤,一辈子都无法抹去,使其中的大多数人几乎和翻译无缘。当然,这不是他们的过错,是那个时代亏欠了他们。 翻译之繁荣也要归功于当时翻译家的献身精神和敬业精神。回望那段时期,不难发现,翻译的条件很差:与国外交往不便,资料匮乏,词典一类的工具书少得可怜,又逢时局动荡,往往不得不携家带口逃离城市,居无定所,难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但他们视译事为生命,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情况下成就了自己的翻译事业。朱生豪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于1936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排除艰深的语言障碍,好不容易译好一部,稿子却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部分被焚,但他并不气馁,在随后的逃难中补齐。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混在排字工中逃离任职场所《中美日报》馆,保住了性命,却丢失了另一部分译稿,随之又不屈不挠地在借居岳父家中时补上。此后不幸染上肺病,身体倦乏羸弱,却仍勉力翻译莎剧,态度一丝不苟,“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合。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见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终于,在1944年基本完成了莎氏全部戏剧的翻译,同时病魔也终结了他32岁的年轻生命。纵观他的一生,17岁进大学,磨砺中英两种语言,为翻译做好准备,24岁开译莎剧,在战火中历时8年,32岁时译竟便猝然离世,仿佛他就是为了翻译莎士比亚才来到这个世界的。其他译家,也多有崇高的职业操守,对待译事字斟句酌,十分用力。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鲁迅的“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后来,傅雷的反复修改甚至重译旧作,都体现了一个译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当然,这个时代的翻译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缺憾:选择翻译对象的无计划性和译著出版的碎片化、白话文不成熟所带来的译文非文非白的尴尬、外文修炼不足和工具书缺乏所造成的误译等等。尽管如此,过往中国翻译的业绩,是亮丽而骄人的。 兴衰难断的今天 我们谈论今天的中国翻译,决不是“兴”“衰”两字所能概括的。随着现代社会的急速发展,经济日趋全球化,国与国之间交往频繁,人口的流动性增大,翻译也愈发显现其作用,助推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人们说及翻译,已经不再囿于笔译,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已使口译的用途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即使是笔译,今天也不光指文学翻译,还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非文学翻译。正因为这样,对翻译现状的评判显得更为复杂,非“兴”即“衰”,非此即彼的说法,无疑会流于简单化。 就口译而言,中国的翻译正处于空前发达的时期。这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谁都知道,中国经济高度倚仗外贸,而如今能够直接使用外语做生意的如凤毛麟角,因此外贸离不开翻译。不难想象,每笔生意后面都站着一个译员,紧张地同外语中特别难缠的数字打交道,不允有丝毫闪失,个中辛苦,鲜为外人所知。他们的总人数非常可观,倘若集结在一起,一定会呈现百万雄师般的壮观,虽然我们在欢庆GDP快速增长的时侯,几乎没有谁会提到,甚至想到,这些幕后的无名之辈,但经济领域口译活动之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 经济领域之外的诸多其他领域呢,如外交、文化、体育、军事、科技等等,哪一方面也少不了翻译,只不过译员的工作多为“隐性”,不大引起注意罢了。如果刻意加以“显性化”,那他们可谓无处不在。君不见,外交使团之间的对谈,总有一个译员在作“二传手”,一面倾听,一面做着速记,脑子里翻云覆雨,奋力用另一种语言,把瞬间记下的内容,不损毫发地传达给对方。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外交活动才显得从容顺畅。文化交流,更是“兵马未动,翻译先行”,同对方的沟通接洽,日程的安排,计划的执行,乃至填表通关等一应琐事,译员几乎全包,自觉地走在前头,扫除语言“雷区”,好让大部队顺利通过。竞技场上,翻译介入尤多,无论是篮、排、足,还是其他中国相对较弱的体育项目,凡有外籍球员或教练的地方,都有译员涉足,他们还往往被誉为教练的“喉舌”,甚至译语到位与否,事关比赛的胜负。至于军事和科技领域对外语人员的倚重,人人都很清楚,无须在这里饶舌了。 说白了,凡是涉外领域,都少不了翻译的支撑,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可以说无处不涉“外”,因而社会对翻译的需求,空前地巨大而急迫。培养译员(者)的基地外语专业也同步快速增长,以英语专业为例,1966年设有该专业的仅74所大学,到了2010年,已增加到了965所。在专业设置上,为顺应需要,破天荒地独立开设了一个“翻译专业”,专门培养口笔译人才。每年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毕业生,少说也有几十万,其中除了少部分从教或转行,绝大多数人都在担任口译。试想,偌大一个中国,该有多少人从事着翻译这一行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多大的作用!以此而言,当今翻译之“兴”,过去任何时代都难以与之比肩。 笔译呢,其概念也起了变化。以往一谈笔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往往被忽视。其实它范围更广,包括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艺学、新闻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金融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自然科学,占了当今翻译的大部分。 自然科学中科技领域的翻译,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几十年来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呈现出职业化和商业化的特点。据中国翻译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我国已正式注册从事翻译服务的公司超过3000家,目前,有数十万人从事这类翻译活动。翻译的语种往往多达数十种,遍涉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经、贸、法、石、汽、食、纺、医药、金融等各个领域。2003年翻译市场的产值为110亿,2005年200亿,2007年已发展到300亿。据此,有人认为翻译服务正在成为文化经济中仅次于教育行业的又一新兴产业。我国多项从国外引进的建设项目,也使科技翻译大大扩容,以上海宝钢一期工程为例,其外文资料重达300吨,译成中文约4亿汉字。又如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一期外文资料重100多吨,译成中文约2.5-2.75亿汉字(上述有关数字,取自黎难秋《新中国科学翻译事业六十年发展简述》)。类似的工程还不少,其外文资料的数量和翻译量,累计会接近天文数字,而由此生发开的翻译活动,绝对史无前例。 我国在1949~2008年间共出版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类译著约50000多种;同一时期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约为23000种。涵盖范围之广,数量之大,涉及语种之多,超越任何时代,翻译界可以面对先贤而毫无愧色。 文学翻译是在读者中影响最大,而遭受非议最多的领域。关于非议,这里我们暂且“按下不表”,留待后面再议,先说说当今文学翻译值得称道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人民对新的精神粮食的渴求,大大刺激了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使此类书籍的出版数量激增。有关资料表明,1949年至1959年间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计5356种,是解放前三十年的两倍多。其中70%为苏联文学作品。改革开放后,文化界摆脱了极左思想的桎梏,审美的鼻子大胆地伸向了以往被视为“糜烂的西方当代文学”,以填补解放后三十年留下的巨大空缺,同时对以往疏漏的外国文学经典进行补遗,出版了在中国长期被隐匿的外国现代名家的作品,如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尤金·奥涅尔、普鲁斯特、萨特、伍尔夫、乔伊斯、劳伦斯、托马斯·曼、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等。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成倍增长。 翻译界还克服了此前(可上溯至二十世纪初)外国文学介绍上零敲碎打、随心所欲的弊端,注意出版的计划性、系统性、完整性,努力把最值得介绍的外国作家以及他们的全貌呈献给读者。横跨前后数十年的三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是一项集全国著名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出版家之力的庞大系统工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等陆续出版,共200来种,囊括东西方文学史上小说、诗歌、戏剧、史诗、理论等不同样式中的精华,展示了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全面了解外国文化的窗子,也为尔后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此外,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外国作家的选集、全集或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选集》(10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9卷)、《屠格涅夫选集》(13卷)、《托尔斯泰文集》(17卷)、《高尔基文集》(20卷)《马雅可夫斯基选集》(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文集》(10卷)《果戈里全集》(7卷)、《屠格涅夫全集》(12卷)《契诃夫文集》(27卷)、《莱蒙托夫文集》(7卷)、《涅克拉索夫文集》(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已推出和计划推出的作品集有《新莎士比亚全集》、《雪莱全集》、《狄更斯全集》、《普希金全集》、《果戈里全集》、《陀思妥耶夫全集》、《屠格涅夫全集》、《莱蒙托夫全集》、《契诃夫全集》、《歌德全集》、《海涅全集》、《卡夫卡全集》、《莫泊桑小说散文全集》、《波德莱尔文集》、《加缪全集》、《泰戈尔全集》、《川端康成文集》、《纪伯伦全集》、《马克·吐温全集》(谢天振、查明建:《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这些全集、选集和文集,卷帙浩繁,蔚为大观,涉及那么多国家和语种,凝聚了那么多翻译家的心血,也只有在太平盛世,国家兴旺,翻译人才济济,经济后盾强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付诸实现。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新时期的翻译及时传递了国外文学信息,供当时急于寻找新的表达方式的中国同行借鉴,外国文学杂志起了尤其重要的作用,其中的佼佼者为《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和《译林》。这些杂志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世界文学》虽然也介绍当代文学,但关注更多的却是传统经典作家,挖掘被遗漏的名家名作;《外国文艺》致力于译介关于当代外国文学的信息,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初,热衷于现代派文学和新的表现手法的速递,介绍了一批技巧新颖、思想前卫而颇有争议的名家,为国内在迷茫中彷徨的青年作家,提供了养料。若干年后的今天,有些作家甚至动情地说,是喝着《外国文艺》的奶汁长大的。这也为后来顾彬的“每一个当代作家后面站着一个西方的大家”之言,提供了注解。《译林》则独树一帜,专注于译介西方通俗文学,满足不同层次的阅读需求,填补了译坛的缺项,也赢得了一大批读者。当然,在传递外国文坛新信息方面,出版社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往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才结束,获奖作家的作品已经递送到读者面前,其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当前的翻译,总体说来,准确性比较高。原因很多,如词典等工具书越来越完备,不像五四时期或者三十年代,好词典难觅,也无力编出像样的外汉词典;互联网检索手段便捷而先进,对比当年,只能依赖很有限的纸质工具书,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很好;此外,改革开放和人们对外语前所未有的重视,使学界总体外语水平有所提高,反观上世纪的前五十年,不少译者或自学外语,或半途出家,真正科班出身的不多。关于译文的准确性,只要比较一下不同时期出版的古典名著复译本,就不难看出,后来的译本在准确性上大大超过前人的译本。当今翻译错误多的恶名,很大程度上来自那几个反复被人引用而绝对耸人听闻的例子,如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把孟子译成孟修斯,把毛泽东诗歌“念奴娇·昆仑”误译为“‘念奴娇’,作者昆仑”。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而且是极为个别,但杀伤力极大,对当今翻译的质量评估产生了颠覆性效应。但如果我们能比较理性地看待现在的翻译,如果我们能俯瞰整个翻译界,就不难看出当代的翻译家在准确性上是超过前人的。 当代翻译的最大缺憾是缺乏大家,缺少公认的翻译佳作。不错,几十年来出版的翻译作品是够多的。走进书店,你会发现,林林总总,目不暇接,听到过的,没有听到过的,应有尽有,但很少有几本书,其文学价值和译文价值,让你感到非买不可。这些年,相比热闹的通俗文化,外国文学经典一类的精英文化,显得很有些寥落。固然,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趋于务实,疏远文学,文化领域越来越娱乐化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但文化自身品质欠佳,也难辞其咎。有些翻译作品没有特色,千人一面,文字没有魅力,缺乏文学性,读之无味。优秀的翻译家,一流的译本少而又少。出现这种现象又有多重原因。尽管当今的译者外文掌握不错,但对译入语的娴熟程度,也即中文表达能力,与前辈差距较大,直接殃及译文质量,因为在对原文理解正确的前提下,译文之优劣决定于母语表达能力。此外,思想保守也是一个原因,我们已习惯于强调思维的同一性,注重一体化,而不是鼓励丰富性和多元化,各种顾虑和束缚太多,译界难以出现百花怒放,多姿多彩的局面。当年钱钟书评价林纾的话:“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如今只信奉译出语和译入语对等的理论。话又得说回来,翻译巨匠的形成,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我们切不可操之过急。 当然,也有极少部分人,缺乏职业道德,与某些唯利是图的出版人联手,炮制劣质译著,抢占市场;有的甚至不惜剽窃他人译作,改头换面出版。单是笔者所译的由译林出版社出的《简·爱》,就被抄袭、剽窃达5次之多。这种现象在译坛时有所闻,但虽然官司不断,却因有利可图,仍屡禁不绝,以致前些年以季羡林、草婴等为首的12位翻译家发出了恪守译德,提高翻译质量的公开呼吁。近期又有读者对新出版的《乔布斯传》不满意,质疑该书译文的质量。这些现象尽管不是翻译界的主流,甚至不过是极少数人的不良作为,但影响极坏,却又剿灭无力,真让人痛心。 孕育着希望的明天 对于中国翻译的将来,我是抱乐观态度的。如今经济振兴,民生改善,国家一方面为了谋求进一步发展,需要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另一方面需要向世界宣示自身形象,进一步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这两方面的需求,都会促进翻译的生长,翻译事业也会得到更强有力的支持,翻译界一定会更有作为。从学术层面来看,条件也是有利的。随着对外交流日趋频繁,外语学习条件大为改善,去海外求学人员激增,以及对外语的普遍重视,我国外语的总体水平将会有更大的提高。同时,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人们对母语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译者所要依恃的中文水平和文化素养,将会有所改善。如此,待以时日,中国的翻译界必将迎来更加欣欣向荣的局面。 但是,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从现在做起: 1. 应该尽快为翻译正名,纠正轻视翻译的做法,给翻译以应有的地位,并大幅度提高译者的待遇和报酬,使整个社会觉得翻译是一个备受尊重,且能得到应有回报的职业。而现实却与此相悖,翻译是一个被人轻贱的行当,除了最高级别的口译,一般译员给人的印象,不外乎领导或老板后面点头哈腰的跟班,一个无异于蓝领光干杂事的雇员。而笔译呢,在高校不视为学术成果,不能算作升等升级、职称评审的依据,译者自然也得不到到应有的尊重,虽然一本像样的译著,其价值胜过如今的不少论文,因为那些所谓“学术成果”,大多东拼西凑,不痛不痒,没有创意。笔译的报酬也很低,一般为1000字50块钱,而译文从初稿到修改稿到定稿,到看校样出书,如果将付出的劳动通算的话,忙乎一整天也不过出二三千字,远不如去外面兼课赚现钱划算。我们不能光责怪今人重利,因为每个社会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才有可能从事其他活动。 2. 高校外语专业是输送翻译人才的主渠道,无论口译还是笔译,译者多半出自高校。外语专业应当为培养各个层次的翻译人才、振兴翻译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目前外语教学普遍重听说,轻读写,学生阅读理解能力薄弱,语言基本功不够扎实,导致翻译时对原文的误读和触目的误译,对翻译带来严重影响。外语专业,尤其是近年来从外语专业独立出来的翻译专业,要加强外语阅读与写作,狠抓语言基本功,提倡博览群书,扩大知识面,多读文学作品,提高对文学的悟性,加强中文修养,提高中文表达能力,不然难以把学生培养成为称职的译者。 3. 译者要自律,要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劳动,需要长期用功夫,具备多方面文化素养,以及全身心投入,即使如此,有时还吃力不讨好,得不到企盼的回报。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好,没有一丝不苟的认真,没有前人所示范的献身精神,不但出不了精品,就连坚守都是困难的。现时的不少误译,以及刺眼的劣作,除了少数为修养不足所致,大多是缺乏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造成的。 4. 出版社应当成为高质量翻译的催生婆,把好编辑和校对关,加强对译文质量的监控。不能光顾着赚钱,只对快餐文化感兴趣,而放弃价值高读者少赚钱不多的经典文化;更不应该为了抢占市场,而组织枪手,短期赶译,炮制劣质翻译。从译著走向市场的过程来看,出版社既是生产单位,又是质检机构,对保证译本的质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方面,媒体也应当协同作战,爱憎分明地褒奖高品质译文,批斥伪劣产品,而不是像当下时行的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为报道对象做软性广告。 5. 国家应出台促进翻译的激励政策。相对文学创作而言,翻译似乎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支持,虽然文化的繁荣绝对离不开翻译的繁荣。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介绍和吸收外来文化,以及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两者都少不了翻译这一媒介,两者都是促进文化繁荣所不可或缺的。目前的中国译界,英译中需要大家,需要精品;而中译英则是译界的软肋,而且后继乏人,不及时采取激励措施,不花大力气扶植,后果将难以设想。 世联翻译-让世界自由沟通!专业的全球语言翻译供应商,上海翻译公司专业品牌。丝路沿线56种语言一站式翻译与技术解决方案,专业英语翻译、日语翻译等文档翻译、同传口译、视频翻译、出国外派服务,加速您的全球交付。 世联翻译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交往城市设有翻译基地,业务覆盖全国城市。每天有近百万字节的信息和贸易通过世联走向全球!积累了大量政商用户数据,翻译人才库数据,多语种语料库大数据。世联品牌和服务品质已得到政务防务和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大中型企业等近万用户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