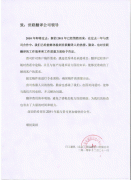余论 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1
时间:2017-07-19 16:03 来源:未知 作者:dl 点击:次
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传媒的合谋使得中国文学的境遇变得越来越“险恶”。虽然优越的文学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倡导仍然一以贯之,虽然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当下文学“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最好时期”的判断仍然坚定而可信[①],而一年一千部的长篇小说以及上万部的中、短篇小说也足以支撑这种“大繁荣”“大发展”的判断,但是大众文学期待的降低、文学接受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作家身份与形象的改变、当代文学史的滞后以及当代文学评价标准的混乱,等等,都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面貌的被“改写”和当代文学地位无可奈何的衰落。与中国当代文学这种发展状况相呼应,对当代文学的研究也面临种种困境与问题,这表现为:其一,中国当代文学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评价体系,极端的、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文学判断再次“复活”,批评界无力让全社会在当代文学问题上形成普遍的共识;其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跟不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节奏,这是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品被视为“无物”或“垃圾”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三,文学评价环境的混乱导致了文学生态的恶化,畸型的社会心理、“暴力”化的文学话语方式的流行使得正常的文学批评已经无法展开。这些或隐或显的困境与问题,在2007年终于因为德国汉学家顾彬那个耸人听闻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的访谈而日益尖锐地暴露了出来[②]。本文将以此为契入点,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做尝试性的分析。
一、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有没有“经典”,应不应该“经典化”?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轻视和贬低,其实早在顾彬之前就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对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学界因为其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度”影响而否定其文学性;对80年代以后以先锋小说为代表的“纯文学”,学界又因其对西方文学的“过度模仿”、缺乏“原创性”而质疑其价值;对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等,刘晓波在1986年9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召开的“新时期10年文学讨论会”上则提出了所谓“新时期文学危机论”,给予新时期文学全面否定。他认为,“新时期文学存有危机,不是五四文学的继续,而是古典文学拙劣的翻版”。在纵的方面,“新时期文学以‘寻根’文学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意识”;在横的方面,“大多数作家作品受理性束缚太甚、呈现出艺术想象力的贫弱,缺乏发自生命本体冲动的的艺术创造力”[③];而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缺乏精神高度”、“价值混乱”、“没有大师”、“没有经典”等的指责也不绝于耳。事实上,顾彬的“垃圾说”不过是以一种特殊的身份把种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和不满进行了集中与放大。而他的“说法”之所以会演变成一个“事件”,也似乎正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不良学术风气的一种放大,因现代化的自卑而导致的对西方的崇拜,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也表现在学术领域,西方汉学家的赞赏会令中国作家身价倍增甚至文学史也因此被改写,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文学神话”的诞生固然是西方汉学家一手制造的,而他们信口开河的“胡说八道”也更能引人注目。客观上说,顾彬的“垃圾说”根本不值一驳,刻薄一点说,他连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言权都没有。他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的阅读量是少得可怜,他之所以敢于煞有介事地诊断中国当代文学的“病根”,之所以敢于对当代文学全盘否定,一方面,出自于他根深蒂固的无知、偏执与狂妄,另一方面完全靠的是中国学术界的西学崇拜所纵容和培育的“学术胆量”。他认为:第一,当代作家普遍缺少对文学坚定执着的信念,以功利和游戏之心对待文学,他们的文学生命短暂如蜉蝣;第二,当代作家普遍缺少外语能力,在这个国际化的时代,只能靠翻译获得国际文学资源,没有真正的国际视野;第三,当代作家普遍不重视写作语言的提炼和升华,没有达到一个作家应有的专业水平,因此是“业余写作”;第四,当代中国作家普遍缺少关注现实的勇气,回避问题,重复历史题材,不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民众的代言人[④]。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以上四点诊断,几乎全是不靠谱的“歪理邪说”。尤其是“外语水平”和“业余写作”的说法简直是荒唐之极,在我看来,汉语是最具有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语言,世界范围内的外国作家有几个精通“汉语”的?他们又怎能成为伟大作家?文学的本质就是“业余”的,文学一专业恐怕就不是“文学”了。而“代言人”问题更恰恰是说反了,自五四以来中国作家就是因为“代言人”意识过于浓郁,才不同程度地牺牲了文学。事实上,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炮轰”,正如北大教授陈平原所指出的那样:“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是哗众取宠,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不是一个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研究分析之后做出的学术判断,而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凭感觉说出来的话。因此,中国作家也没有必要太在意。”[⑤]
然而,我们可以不理会顾彬的“炮轰”,却不能不反思中国文学界内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根深蒂固的轻视与否定。从五四中国现代文学开端到现在,中国文学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但是对这百年中国文学的认识,学术界似乎一直都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认同似乎也仅限于现代文学三十年。而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了近60年,两倍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但却笼罩在现代文学的“阴影”中,一直陷于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窘境之中,学术界很长时间宁可前赴后继地去“研究”、“挖掘”、“重新发现”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二流、三流的作家作品,也不愿正视当代文学的成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没有经典、没有大师?还是种种偏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不能发现和认识经典与大师?这是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界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真的没有经典、没有大师,我们的文学“大繁荣大发展”不就是虚假的繁荣,不就是一句空话?这60年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的不就是一个可怕的空白?如果有经典也有大师的话,那么阻碍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症结又是什么呢?首先,我觉得,厚古薄今、轻视当代、“文人相轻”的心理自古就有,而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界尤其严重。其次,“当代人不宜写当代史”、“当代文学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检验”、“当代人与当代文学之间没有必要的距离”等等文学史观点也阻碍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其三,从大学的学术体制来说,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学者的“崇拜”是当代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普遍状况。这是因为现在学科体制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是由研究现代文学的一批杰出学者开创的,“重现代轻当代”是理所当然的。当代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衍生品、附属品,不仅其成就会自然而然地被看低一格,而且研究队伍也无法跟现代文学的队伍相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各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力量与“当代文学”研究力量的不平衡一直是一个显著的问题。不仅如此,甚至当代文学研究本身的价值也常受到怀疑。许多人认为对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与研究没有学术性、没有“学问”,正如陈晓明先生所言:“文学批评在大学科目里没有位置,因为大学教授都不是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很难跻身教授行列,这样一个矛盾使大学的文学研究与现实的文学创作相隔绝。”[⑥] 可以说,正是如上种种主客观的原因造成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误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与历史化过程。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最为辉煌的篇章。无论是从汉语本身的成熟程度和文学性的实现程度来看,还是从当代作家的创造力来看,“当代文学”的成就多要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没经典、没有大师,而是我们对于经典、大师不敢承认。正如王尧、林建法在其主编的“新经典的文库”序言中所说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偏见和无知,不仅来自‘外部’的影响,也同时在受到‘内部’的干扰。这些影响和干扰,使许多人不能正视这样的事实: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因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理直气壮地去筛选、研究和认定那些涌现在我们身边的“经典”正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是可悲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呼唤和确立当代“经典”。当然,我们也要承认,“经典化”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是凭热情和冲动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但我们至少应该完成认识论的“转变”并真正启动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澄清几个误区:
其一,对于“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误区。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既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又是一个无法进行精确检测和证明的修辞性概念,因为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因为各自的角度、背景和趣味、修养等的不同,他们对所谓“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等等词汇的理解也可能完全不同。应该说,经典既有客观性、绝对性的一面,也有主观性、相对性的一面,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确的是,“经典”不是十全十美、无可挑剔的代名词,在人类文学史上似乎并不存在毫无缺点并能被任何人所认同的“经典”。因此,对每一个时代来说,“经典”并不是指那些高不可樊的神圣的、神秘的存在,只不过是那些比较优秀、能被比较多的人喜爱的作品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中国文坛谈论“经典”时那种神圣化、莫测高深的乌托邦姿态,不过是遮蔽和否定当代文学的一种不自觉的方式,他们假定了一种遥远、神秘、绝对、完美的“经典形象”,并以对此一本正经的信仰、崇拜和无限拔高,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伦理话语体系与道德话语体系,从而充满正义感地宣判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死刑。我们有趣地看到,“经典”的神圣化和神秘化在此又演变成了“经典”的伦理化与道德化,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根本性障碍。
其二,“经典”的“自动呈现”误区。与对“经典”的神圣化和神秘化倾向相呼应,许多人宣称经典是自动呈现的,经典的价值是先天具备、无须命名的。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等生活哲理似乎也证明了这样的观念。但是,这样的观点恰恰又忽略了文学“经典”的特殊性,文学经典是在阅读的意义上体现其价值的。一个没有被发现的经典,一个没有被阅读的经典,一个没有对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影响力的经典,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能正式出版、发表、流传的作品只是极少数,而可能有大量的文本会因为编辑、审稿体系或其他原因而无法面世,这些没有面世的作品中可能就隐藏了无数的经典杰作,然而,这些经典杰作无论多么伟大,因为它没有现实化因而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的。而对于已经被认可的经典文学作品来说,它的价值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阅读者,经典完全可能呈现不同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的价值不仅不是自动呈现的,而且更是需要不断地被发现,被赋予,被创造,被命名的。一个时代的作品,如果没有被同时代人阅读、研究、评论、选择,那么,这个时代的“经典”是不会自动“现身”的。在对经典确立方式的认识上当下文学界存在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错觉:即,“经典”只是过去时代的作品,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和轻视当代,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这实际上就“人为”地阻隔了当代人、当代文学通向经典的道路,并以“悬置”的方式剥夺了当代人认识和言说当代经典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阻隔”面前,当代人正在逐步失去对当代生活和当代文学的信心,我们仿佛不是生活在当代,所谓当代,所谓当代文学似乎都成了一种“缺席”的、不在场的存在,更不要说当代经典了。这种对于当代文学变相的“虚无主义”可以说也正是当代文学面孔暧昧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最为核心的就是命名权的问题。在当代文学经典的确认和命名问题上,当代人常常被剥夺了命名权。我们总是把对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的责任推给时间和后人,我们总是以时间沉淀不够、距离太近、情绪视角的影响等等理由延宕对当代文学经典的命名。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换句话说,即使它被后人“考古”挖掘为“经典”,那它对所处时代的读者也是毫无意义的。我很难想像一部对它所处的时代和它所处时代的读者毫无精神影响的作品会成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早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已被认可了,只不过建国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当代人、同时代人的命名更可靠,更不可或缺。不仅,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而且每一个读者也应该是一个“经典”的确立者和命名者。实际上,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它不应是“过去时态”,而应该是“现在进行时态”的。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阅读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世联翻译-让世界自由沟通!专业的全球语言翻译供应商,上海翻译公司专业品牌。丝路沿线56种语言一站式翻译与技术解决方案,专业英语翻译、日语翻译等文档翻译、同传口译、视频翻译、出国外派服务,加速您的全球交付。
世联翻译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交往城市设有翻译基地,业务覆盖全国城市。每天有近百万字节的信息和贸易通过世联走向全球!积累了大量政商用户数据,翻译人才库数据,多语种语料库大数据。世联品牌和服务品质已得到政务防务和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大中型企业等近万用户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