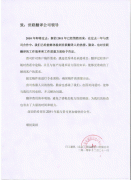韩少功的翻译和我们的昆德拉2
时间:2017-07-26 15:44 来源:未知 作者:dl 点击:次
在“原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读者”这一关系链条上,最复杂的关系纠葛恐怕还是在原作者与译者之间——尤其如果原作者是一位在世作家的话。因为译者可以不在乎读者的反映,这倒不是说他们往往被限制在接受语之内,或者对翻译至多发表一些非专业的意见,更重要的是,读者往往是一个不确定的人群;而原作者则是唯一的原文本创造者和法律权益所有者;这两方面同时造就了传统翻译观念中的原作者权威观念。这样我们不妨问一句:原作者的认可,真可以作为译本忠实性的担保吗?
果真如此的话,韩少功所依据的英译本,同样曾经是昆德拉认可并给予高度赞扬的。这就要说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美国英译者迈克尔•亨利•海默(Michael Henry Heim,1944—)及其与昆德拉之间的矛盾纠葛了。
这位海默教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斯拉夫语教授,不仅先后从捷克语翻译了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玩笑》(The Joke)、《笑忘书》(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及戏剧《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and His Master),还从德语翻译过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 By Thomas Mann),从俄语编译过《安东尼•契诃夫的生平与思想:书信选注》(Anton Chekhov's Life and Thought :Selected Letters and Commentaries)等,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多产翻译家和斯拉夫语文学者,其译作不但得到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的认可——他翻译的捷克作家丹尼洛•契斯(Danilo Kiš)和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的作品广受赞许,而且也曾经是昆德拉最信任的译者之一。
早在七十年代末,海默曾把被《玩笑》英国译本(由伦敦的MacDonald和纽约Coward McCann同时出版)所删除的一章专门译出,并发表在一家学期刊上。之前,昆德拉曾在《泰晤士文学副刊》发表公开信,抗议英国译者擅自删节其中的重要章节,他显然被海默“这种对受到虐待和羞辱的文学表示同情的高尚举动所深深感染”了。于是有一天,一位名叫阿伦•阿舍(Aaron Asher)的年轻人来敲响了海默教授的门。阿舍是Harper & Row出版社的编辑,受昆德拉之托来邀请海默担当英译者的。在阿舍的建议下,1980年海默翻译出版了《笑忘书》(由Pengain Books出版)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同时取得了文学和商业两方面的成功,也进一步赢得昆德拉的信任。1982年,在昆德拉连获两次“大英联邦奖”之时,海默翻译的《玩笑》出版,昆德拉甚至这样称赞道:“对一本讲述强奸故事并屡受侵犯的小说而言,这是第一部公正可信的译本。”
1982年底,昆德拉完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捷克语写作,两年后,法译本出版,紧接着,海默的英译本也在美国出版,并获洛杉矶“时代丛书小说奖”。之后的两年间,昆德拉喜事不断:1985年他的戏剧《雅克和他的主人》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剧作得以公演,随后又获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1986年成为美国艺术学会荣誉会员,并获诺贝尔奖提名。所有这些,应该都离不开海默的一份贡献。从此,昆德拉开始跻身当代国际著名作家之列,在西欧和美国的声誉如日中天,而我们的韩少功,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美国。
不过,伴随着昆德拉日增的声誉,译者与作者之间的矛盾却日渐加深,这主要源于昆德拉所经历的两次《玩笑》翻译事件。继上面提到的发生在六十年代末的《玩笑》英国译本事件十年之后,昆德拉再次遭遇了《玩笑》法译本事件,这时他已定居法国。当1979年的一天,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记者阿兰• 芬凯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在采访中问他,为什么他最近的小说失去了《玩笑》那种“华丽”风格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再一次被草率的译本所“劫持”了。因为他的捷克语写作向来追求一种近乎中性的缓和风格,轻松而不失准确,颇有几分家庭医疗手册的味道。怎么就成了一种“华丽”语体了呢?!当晚,他找来马赛尔•艾莫南(Marcel Aymonin)的法译本仔细研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位马赛尔有一种夸张得离谱的矫饰嗜好,比如喜欢把“天空蔚蓝”添油加醋地译作“淡蓝色的天空下,十月举起了它华丽的盾牌”,诸如此类。
于是昆德拉开始了漫长的与翻译的抗争之路,甚至着迷于与他认为不忠实的翻译作斗争。其实,作为移民作家的昆德拉,特别重视译本的忠实性尤其特殊的道理,因为他深知,捷克语读者只占其读者群的极少部分,“我的书是以翻译形式存在的,这些译本被阅读、评论、评价、接受或者拒绝,我怎能不关注翻译”呢?不过他也曾意识到,任何翻译都无法实现完完全全的对等关系。在捷克语版《笑忘录》中,他就以捷克语lítost(遗憾)一词为例,说明它在其他语言中无法找到真正对应,由此认为理想翻译的不可能实现。但后来当他发现自己的“不可实现”之说正好成为那些粗陋译作的托辞时,他被激怒了,进而即便对自己曾经信任的译者也多疑起来,以至于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海默就是这些译者中的一个。
其实,早在海默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过程中,昆德拉就在用捷克语与海默讨论译稿的同时,又用英语和法语与编辑阿舍进行不厌其烦的探讨,并表现出对译文与原文完全一致性的追求。随着昆德拉“译本完美主义”的日益膨胀,终于因《玩笑》英译本的修订事件,与海默这位多年交好,并为他在北美乃至全世界带来声誉的出色译者断交了。1992年,昆德拉借在Harper Collins出版“阿伦•阿舍丛书”之机,在海默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编辑阿舍一起对海默译本做了大量修改,这种修改甚至令阿舍也厌烦起来。昆德拉后来强调,作家修改自己已写的东西,这种行为非常具有创造性。当阿舍把修订稿校样寄给海默时,这一次轮到海默生气了,他提出了抗议:“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而作出修改,因此我拒绝署名。”后来出版的修订本上因此没有列出任何译者的名字。
其实,作为冤屈的昆德拉译者,海默并不是第一个,也不算最后一个。在找到海默之前,昆德拉就对自己所信任的第一个美国译者发生过怀疑。这位名叫彼得•库西(Peter Kussi)翻译家曾从捷克语翻译过《生活在别处》(Life Is Elsewhere)、《告别圆舞曲》(Farewell Waltz,英译为The Farewell Party)及其他短篇小说。而在海默之后,昆德拉又与再度请回来的库西因为《不朽》的翻译和《告别圆舞曲》的修订而断交。用《世界语》(Lingua Franca)杂志资深编辑凯莱布•克雷恩((Caleb Crain,感谢清华大学郭昱教授提供的材料)的话说,昆德拉的斗争固然取得了效果,也付出了代价。他是否在为达到一个不可企及的理想而损害自己的作品和声誉呢?
如此看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英译过程,倒应该是昆德拉与海默最融洽的一次合作了,而韩少功的中译本所依据的就是海默的英译,1984年纽约Harper & Row出版社出版。
现在我们试着设想一下这样的情景:八十高龄的昆德拉发狠学习汉语了,并取得了如他的法语、至少是英语那样的成绩(七十年代初起,昆德拉向妻子学英文,1975年移居法国后开始学习法语),总之能读懂中文了。这时候他对韩少功和许钧的两个中译本会有怎样的判断呢?一个是从英语“非法”转译却使昆德拉在十几亿人口的中文世界里声名大振的译本,另一个是从自己亲自参与修订的法文本转译、获得自己授权但对读者的影响长期无法盖过前者的译本,他更倾向于哪一个呢?我们能保证他一定喜欢后者吗?或许韩少功与许钧一样,都免不了与昆德拉“断交”的可能吧。
其实,文学翻译在整体上当然应该始终以传达原著的意图为宗旨,但这并不否认译者的创造性因素,而这种创造性的发挥,是在忠实与自由的两难处境的夹缝中展开的。如果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译文即便能被理解,也难免支离破碎;但若自由地调整原作的结构,以便达意清晰,就有可能丧失成就其文学作品个性的语言细节。
作为原作者,昆德拉追求译本的质量本没什么错,甚至强调作者对旧作的修改权及其创造性也无可指责,但他因此又否定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权利(这种权利同样是无法也无力剥夺的,除非原作者亲自出马,用不同的语言将原作重写一遍)并追求绝对的忠实,这其实是一种文学翻译的乌托邦狂想。巴别塔既然无法在人类整体历史中存在,当然更无法在个体身上实现。他从对翻译质量的必要警惕开始,一路下来,最后发展成对已经进入传播和接受流程的文本之权力欲的无限膨胀,甚至对翻译主体之创造性的无条件褫夺,是不是出于一个来自弱势民族的流散作家的一种跨文化飘泊的焦虑呢?但是,他管得了法译本、英译本,还能管得了生前生后、已有将有的各种语言的所有译本吗?
写到这里,作为中文世界里众多昆德拉爱好者的一份子,我不禁感叹:幸运的韩少功,冤屈的海默,无奈的昆德拉!
世联翻译-让世界自由沟通!专业的全球语言翻译供应商,上海翻译公司专业品牌。丝路沿线56种语言一站式翻译与技术解决方案,专业英语翻译、日语翻译等文档翻译、同传口译、视频翻译、出国外派服务,加速您的全球交付。
世联翻译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交往城市设有翻译基地,业务覆盖全国城市。每天有近百万字节的信息和贸易通过世联走向全球!积累了大量政商用户数据,翻译人才库数据,多语种语料库大数据。世联品牌和服务品质已得到政务防务和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大中型企业等近万用户的认可。 |